 |
| 中尉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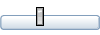 |
註冊時間: 2004/09/14 AM 12:13:46
文章: 1775
性別: 
|
這是從韓天衡先生在1995 年12月出版的《中國篆刻》季刊第四期裡,所發表的文章轉錄來的,對於內容並沒有做任何增減,只是從簡体字變成繁体字。不過如果有我自己的意見,不一定是對的^_^|||,會在文章後面用﹝﹞來做區別,也請大家不要搞混了。
用刀的本質是求所鐫刻線條的圓健。圓則有厚度,健則有力度。對此,我嘗有一比,線條無論是直曲,都當如枯藤之纏繞,不因卷曲而失其圓健(圖一)。若卷曲處失之圓健,則如麥桿之折疊,圓之趣喪失殆盡,論之以用刀,為下下品(圖二)。
〔線條不管如何跑,都應該注意”氣”有沒有”順”。這跟書法講求行氣,有點類似。〕

嘗聞老輩曰:「刻圖章就是將不要的地方剔去(指朱文)。」吾初亦遵此道。後始悟出了運刀的任務是使線條完美地保留下來,其次才是把「不要的地方剔去」。換言之,運刀的力量要完全地傳遞并收容于線條中,而不是將力量隨著石屑白白地失去。此中區別雖微,實有主次、本末之異,不可不作純清。吾近治巨印「登山小己」似有會心處。(圖三)
〔我想初學者先要學的也是先把不要的地方挖掉,不管是朱文還是白文。不過已入門的人,應該要好好去体會韓天衡先生這句話。〕

用刀產生的藝術效果,取決于運刀之角度、節奏、力度,也關乎作者的天賦和氣質。後者學而能者,,而前者為學而知之,知而能之。一般說來,用刀一如用筆,中段多能圓健,而其薄削往往于起訖處更易窺出。若以一根直線條論之,兩端呈燕尾,易墮入薄削感(圖四);兩端呈直角,易產生平板感(圖五);兩端呈微圓,易出現醇厚感(圖六);中段呈外凸狀則覺飽滿,但也會產生臃腫感(圖七);中段呈內凹狀則覺勁挺,但也會出現輕佻感(圖八)。然而,一字乃至一印有許多的筆道組合,如何交叉組合,其中更有大學問在。
用刀一途,素來為行內有爭議的命題。明清印人,居然刀握於手掌間,而大言用刀之無足輕重,頗滑稽。然也有印人,神化用刀者。明人陳赤即創有「直入刀」、「借勢刀」、「空行刀」、「徐起刀」、「救敝刀」之說,其義玄幻之至。清人姚晏又有「十九刀法」之說,許容對用刀有「十三法」之論,不一而足。錢松為用刀大師,風神出邃,至今無匹。他對用刀有明白透徹的認識。其於「蠡甫借觀」一印邊款中稱:「篆刻有為切刀,有為沖刀,其法種種,餘則未得。但以筆事之,當不是門外漢。」錢松的這段論說,仿佛在告誡我等:對刀法的極度輕蔑者,以及對刀法表述的極度神化者,都是對刀法這一命題的真正的不明白,不理解者。嗚呼!
〔線條的粗細、形狀,並不可就這麼決定。我認為應取決整個印章的安排、風格、字体等等。現代薛平南老師的印章常常可見”燕尾”,這是薛平南老師印章的特色。〕

運刀速度與石質有關,但在一般情況下,速度關係到線條的力度、厚度。運刀過快,産生的線條呈粗鋸齒形,近於燥(圖九);運刀過慢,線條黏結若死蚓,近於僵。初學者不妨在石料上多作實踐,逐漸把握到自己適應的用刀速度,乃至用刀的角度和力度。又,用刀有雙刀與單刀之別,雙刀求其線條蘊藉,單刀求其線條猛利。吾中歲治雙刀白文印,往往一刀重入,取其勁,而反向一刀則在鋸齒形之近裏側處輕入,如此,則溫潤中略見犀利,吾嘗自謂爲「一刀半」者(圖十)。
篆刻鈐於平面的紙上而能注入浮雕般的多層面的情趣,這是刀的魔力所在。再直言之,乃印人之魔力所在。
明人有多重篆法而輕刀法之論。然篆者爲書法,刀法爲鐫法,書法與鐫法的結合方爲篆刻,故不可輕易重篆輕刀也。
明朱簡有一「使刀如筆」之論,頗精當。用刀當有筆意,方見書法之韻,然筆中依然要見刀,從而得生辣峭爽之意,刀筆相輔助,方爲佳構。
〔運刀的速度除了和石質有關,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:個人的風格。如何去掌握運刀的速度,那就得由刻的人自己去体會了〕

刀不爽,印就爛。刻要爽挺,局部可漫漶,吳缶廬深諳此道,較得燦爛之致。今人不曉其中機關,視爽挺爲削薄,以破碎爲厚重,傷本失神,其作必爛而不燦。
用刀之妙,讓之蒼渾,得之功力;撝叔巧麗,得之天份;三庚鮮挺,得之嫺熟。昌碩高古,得之整飭;白石猛利,得之臂力;叔蓋蒼渾,高古兼嫻得;牧甫華潔,勁麗並施,皆為近世印壇巨匠。(圖十一~十七)







近人治印,用刀以瘦鐵為第一人。其出自缶公而悖行之,重刻而輕做,一任自在,天趣獨蘊。瘦鐵用刀善用勒法,力皆能轉遞生發於線條間,加之刀之善運,腕之善轉,故獨多韻致,即使章法稍次,而其線條間刀味十足,盎然感人。(圖二十,二十一)


用刀如用筆,筆有八面用鋒之妙,刀亦然。以愚所悟,用刀之妙在於用好刀角、刀背兩部位。交錯替換用之,三法則生百法,自具音樂節奏、起伏、抑揚、陰陽之妙。此中三昧,古來知者不多,用者亦渺。以世傳作品論,鄧完白、吳讓之、錢松當為解人。惜未能以心得留傳後人,古來用刀憾事,無過於斯。
用刀佳境,不在破,不在鈍。破也可導致瑣碎,鈍也可導致僵板。綜觀古來佳作,破也能圓滿,不破也自圓滿;鈍能得古醇,而不鈍也能得之古醇。故用刀當不以形式手段障眼,求得內理自當成家。要在通曉個中三昧,以自然心作天成相,刻意乃至於無意而生意為極詣。
執刀因人而異,不必求同,也不需求同,此一如書家之執筆也。昌碩執刀由外向內側運刀,介堪由右向左側運刀,日人梅舒適由內向外運刀。又運刀之用角,又有內外側之別,介堪多用內側,巨來多用外側。故執刀運刀各有路數,不必僅以方法較厚薄優劣。又姿勢各異,於風骨必有關係,我輩不可不知。
自明人興起治石章、治印之術,用刀皆為開挖一層空間,即使求破求碎,也未有超脫者。自缶廬出,得封泥瓦甓之啟示,刻而後做,做印非解決刻之不足,而是解決刻之不能,遂使線條有浮雕感,遂開印面兩層空間。此功不可歿也。故對缶公所稱「道在瓦甓」,吾輩當深刻領會之。
〔線條的粗細、形狀,印章的破或不破是一個值得好好去探討的東西。太過有時就會變的支離破碎;保守卻有時顯得綁手綁腳。多看看名家的作品,多摹刻自然會有更深的体會。〕
趙仲穆印,用刀一等。飄逸中寓肅穆之氣,殊為可貴(圖二十二,二十三)然其篆法、章法乏己意,故終不為大家,令人扼腕嘆惜。
趙撝叔嘗稱:「古印有筆尤有墨,今人但有刀與石。」筆者意趣、風韻、胸次之謂也。故刀落石開之際,不可牢記筆墨之注入也。要之,治一佳印,筆、墨、刀、石缺一不可。


用刀之妙,妙於心手相應、方圓悉從。更妙在生刀外之意,由印之小如棗粟而擴就為籠罩胸第的大千世界。近人有專治巨印而自詡者,然不知,巨印之巨,非材料之大塊,而在於用刀之大氣,境界之拓展。讀錢松、缶翁佳作,小印多有尋丈之勢,此乃真巨印者。
趙撝叔稱:「漢銅印妙處,不在斑駁,而在渾厚,學渾厚則全恃腕力。」又謂:「此事與予同志者杭州錢叔蓋一人而已(圖二十四),叔蓋以輕行取勢,予務為深入,法又微不同,則其成則一也。」然用刀務為「深入」與「輕行取勢」法不同,則其成也不一。叔蓋之遠較悲庵印「渾厚」是世有定論的。治印大師若撝叔者(圖二十五),居然於用刀也乏深解,可見此技之神奧莫明矣。


黃牧甫用刀尚光潔,一生身体力行。然觀其用刀或節奏時快時慢,線條之或粗或細,或排列之欹側鬆緊,或白文之自筆道外起已留刀痕,或朱文之起訖處留碎朱屑,頗多出新手段。故光潔其表而骨子裡豐而富之,離而奇之,不擇手段。師牧甫者不諳此道,則必然由師其光潔,而墮入光滑之途。
用刀,吾意尚淺。非淺之必得醇厚,適度的深刻往往也可得之醇厚。然淺之得醇厚較之深入得醇厚為便易也。淺刻則線條坡度較坦,鈐之於印泥則結口處由深刻的「十分明確」變為「近乎明確」,這樣則利於產生視覺上的模糊感。而從審美的角度講,模糊感則近於渾,近於厚也。
刻印有擱刀而不再修飭者,介堪是也;刻印初成而反覆修飭者,巨來是也。用刀穩健,落刀即到善處,是為本領。印初刻成,能反覆修飭而無雕鑿氣,是也為本領。唯不同者介堪師能日就五十印,而巨來則不能矣。
錢松印筆筆圓厚,推想其刀口當近月芽型(圖二十六);讓之印起訖處別於他人,推想其刀當非平口型,而似斜角型(圖二十七)。然吾輩去古益遠,不能起兩翁而請益之。若謎之百思不得其底,大有欲解不得、欲罷不能之迷惘失落感。


運刀貴在大膽,放膽縱橫,走刀出血不足懼。從某種意義上,刻印不出血,不足以成為大印家。
初習印藝,素以秦漢為典範,此論無疑。然秦漢印出自鑿、鑄或琢,故今人臨摹秦漢印於用刀當參習明清名家印作,方稱至善。
刻印用刀,宜淺而不宜深。刻線如挖溝,此必礙刀之揮運。淺則刀利於起伏使轉,易得運刀若筆之妙。然淺刻之難在於見刀發力,於醇厚中得挺爽風骨,以不膩不爛不糊為貴。
印人揮刀五百春秋,集古來方圓兩大流派之大成者,當數吳熙載、錢叔蓋。方虛谷有語:「淡中藏美麗,虛處著工力。」此兩人足以當之。吳、錢兩家用刀雖有主衝與主切之別,然不同的兩極往往有相同的淵源。兩家皆尚淺,淺則調動幅度大,游刃之恢恢,可變幻氣象;兩家皆尚鬆,鬆則意態從容,心手相符,自在天然少作家氣;兩家皆尚生,生則拒甜抗俗,不襲陳式,耐於咀嚼。用刀淺、鬆、生不易,得此三字則法外有韻,回味無盡。
〔總括來說,用刀一途,在韓天衡先生來說,他是主張刻淺的。不過我認為在開始學的過程中,應該各種都去嘗試看看;以我而言,我到現在的習慣還是刻深。〕
吾曾於用刀作衝、披之論,多有咨詢者。衝、披之法,風味大異而消息微茫。我以為要者:衝者運刀時力發於刃之後端,呈推勢;披者運刀時力發於刃之上方,呈由上遞下之勢。此語近於玄奧,而穎者當可玩味之。然衝、披兩法當兼用之,以吾心得論,直驅多衝,轉折多披。
用刀之妙在於一刀在握,長驅直入,一無呆滯。但一味直入則痛快有餘,蘊藉不足,學木居士易墮此途。缶翁中歲佳作,用刀爽而不滑,澀而不滯,厚而不板,古而不舊,露蓄兼備,令人讚佩無已。
用刀缺乏肯定感,以破補借,謬也。運刀在腕,刀自有眼,當以刻為第一義。
用刀太直、太深,刻石如挖溝,線條犀挺而易失之刻板。用刀太淺、太側,刻石如削皮,線條渾脫而易失之浮腫。直深而拒刻板,汪關、林皋得之。淺側而拒浮腫,吳熙載、錢松得之。得其優而汰其弊,始稱大匠。
當今已故老輩,用刀余最服膺錢崖,雄、峻、厚、重,且發之自然,豪跌而一無嬌柔做作氣。即使置於明清兩朝大家間,亦堪稱梟雄。
刀有厚薄、輕重、短長、銳鈍、方圓、大小之別。因人而異,不必求其定式,毋須硬擇高低。刀式為器具,以有高妙之用刀技法方能名世,然不可不知器具之作用。刀具關係風格,故古有「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」之說。然不可不知惟刀具是問之弊端,即使以缶翁為我用,所作也決非缶翁印。故民諺復有「好將不揀槍」之說。
線條的力度生發於對阻力的突破,故沒有阻力即沒有線條的張力。運刀之際,受阻不進則滯,破阻而入則勁,似無阻力而橫衝直撞必流於浮滑。
運用之法,晚明人已大備。汪尹子善用衝,朱修能善用切,何主臣衝切兼用,蘇嘯民偶施披法,遂開清季千姿百態之法門。若林皋之與汪關,丁敬之與朱簡,鄧石如之與蘇宣,皆顯見師承痕跡。
汪關刻朱文印,於線條交接處多加粗,吾曾喻之為「焊接點」,使印作於娟秀中得醇厚意。竊以為汪氏此舉,一得之於漢鑄,二体會於感官。(圖二十八)
缶翁善作印,前無古人。來負翁也善做,得宏闊氣勢。然缶翁之做,由苦心雕刻而歸於天然自成;負翁之做,由苦心雕刻而留有雕刻跡象。故當以缶翁為不易也。(圖二十九,三十)



印有朱白之別,唯古璽或朱或白皆能妥貼。繆篆宜做白文,小篆宜作朱文。繆篆能作朱文印者難,小篆而能作白文印尤難,古來少有成功者。
用刀之妙,妙在直線條以曲求直,又妙在曲線條以直求曲。得此訣者則下刀不妄,自具內涵,所謂刀筆下有物事者。此義理自可從缶翁中年印作、讓翁晚年印作中悟得。
牧甫用刀,白文多自線條外入,每每留細微刀痕,此法乃出於熙載(圖三十一),為牧甫窺出且發揚之。此為其近不惑時事也(圖三十二)。此刀痕雖若有若無,而與其筆道粗細相映,別具意趣。其治朱文印多從鏡文中引伸發揮,起訖處偶留石屑,起筆或方入,或重入,其義理則同於白文也(圖三十三,三十四)。




用刀固有定法,然也有見機行事者。若石澀,宜用刀挺爽;若石脆,宜用刀怠慢;若石有砂釘,則如入地雷陣,用刀務必步步為營方是。
古鑿印常見刀痕,而以含蓄為貴;古鑄印多見含蓄,而以有刀味為貴。(圖三十五~四十)






〔用刀的手法、工具,因人而異,只要用的習慣就好了。不過我還是建議初學者買一支比較好的刀,因為當刻到比較硬的石材時,就不會刻的手痛了。〕
往昔吾海居甌水,每每窺漁人搖櫓,其勢上下反側,綢繆盤旋,而輕舟飛發,曲直如意。由此,漸悟線條直生於曲、曲生於直、曲直互用、互為表裏、互為形質之理。借搖櫓之法而運於刀,線條似別于古賢。(圖四十一~四十六)






撝叔用刀,小印勝於大印。其作小印,用刀動遽飛發,刀逼線條,不畏線條之存亡,所出線條多有斷離處,極具「筆不到意到」之妙。(圖四十七~四十九)



漢官印多鑿成。金印性較銅質為嫩,細審其鑿痕,可知鑿具不大,鋒窄刃平而薄。故每在線條轉折處需一改大刀闊斧手段,其刃徐徐漸入,有鑿痕疊進狀。惜至今猶未見其時鑿具,不能驗吾見地之是非。
印之力度,以刻出之點劃線條為唯一檢驗尺度。腕力強,非即能令線條發力。腕強而不善用,線條或燥或爆,失盡內力;腕強而善用,腕力授於刀,刀授於刃,刃授于石,複注入點劃線條間,必能真力彌滿。故善用力者,力百斤而能發千斤;不善用刀者,力千斤則喪八百。此中訣竅不可不深究明察之(圖五十)。

〔用刀的方法,或許是很難,但是我還是希望大家能用心去体會,畢竟用書面的方式是很難去表現的,最好能親自觀看名家現場示範。〕
|
|



